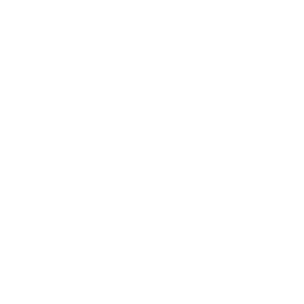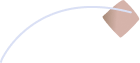GOOGLE退出:2010年第一個企業“行為藝術”
GOOGLE擬退出,制造了中美兩種文化在歲末最大的不兼容性,無論是出于商業還是摻雜美國白宮的政治目的,GOOGLE都到達了中國的反應期頂點。它沒有隱忍,這點上看它是堅持自己的商業自由性與選擇權,而中國在這個反應上也毫不客氣的遵循了本國的法律原則,因而后者不認為GOOGLE的選擇是中方的問題。
作為理想主義者的GOOGLE在中國情感上很寂寞商業上很挫敗,這是注定的,它忘了一個特色“原則”:因為越是開放性的東西在發展中國家是需要確認的——而不是無限量開放的——技術是可控制的,管理就成為了一道似乎必須的程序。未來是需要代價的,中國的古諺語不是白講的,美國人來中國做企業還是學點家樂福的精神,可能會更現實一點——當然這一點上就純粹為商業利益了。
GOOGLE當然很敏感,它骨子里甚至流淌了自由藝術家的血液,它開始了一次瘋狂的也符合自己商業用途的行為表演,這是考驗中美兩國高層也是普通網民的智慧和意識,非常嚴肅又非常有趣。
我寧愿相信,這是一個來自美國企業也是最徹底貫徹全球化企業的一次中國版終極“行為藝術”。我不太認為GOOGLE會拿中國這么大一個市場隨意“作秀”,而且將對象明確的指向中國政府。我覺得是美國商業文化的認真一面,GOOGLE想通過這樣一次可能付出巨大代價的“行為藝術”,能夠與有關方面進行一次談判。它要知道自己判斷這個新世界生成的“誤差”有多大,這是開放狀態的GOOGLE極想知道的。這是我對GOOGLE退出“行為藝術”的判斷。
因此,從藝術的角度上可以推導出來的結論是,GOOGLE退出是藝術行為,而不是商業作秀。還可以推導出來,如果GOOGLE退出對網友精神是要造成或長或短的創傷的。
GOOGLE代表的是美國的一種新經濟商業模式,這種模式特征性在于越是運用越帶來全球的開放性,而且更是一種互動性的新生活方式。但是在中國這一切要有一種適度的原則,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這個領域,是極為特殊與敏感的,而GOOGLE卻正在有意觸碰和反感這一點,它沒有考慮到中國文化對于新經濟——特別是帶有意識形態的產品是極為謹慎的,這之間產生了看似不可兼容的矛盾,但是這個矛盾正如GOOGLE的要義,它可以生成更多新的東西,因而又可以超越的。
這是凸顯的矛盾,是全面邁向全球化新經濟化過程中,中國文化面臨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我們這里舉兩個例子:
GOOGLE和微軟都是美國新經濟的代表,但是兩個版本已經完全不同了。比如GOOGLE倡導的包容性與開放性原則,是微軟所不能比擬的,換個角度上看,GOOGLE是新未來信息時代的主要整合平臺之一,相對前者而言,有分析文章已認為,微軟很可能退化到一個傳統的具體的平臺里。
GOOGLE不可能違背它在互聯網當中的開放性原則,這是它的框架和血液,而微軟最后只是硬件提供商性質的平臺,我們選擇GOOGLE,是選擇更新形態的美國,這正是中美文化的新未來。而GOOGLE作為新經濟的代表,它需要中方彈出一個更大區別于老派的微軟的空間出來,這也是新文化的一次突圍的反應,這就是GOOGLE要退出做行為藝術的“完全版猜想”。
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如果沒有了GOOGLE,一時還很難讓網民們交代,這個問題當然要被論證,因為隨著中國新一輪經濟發展,總有聲音在表達自己可以制造一個“GOOGLE”出來——這種觀點是非常荒唐的,很多東西形成的價值觀念,已經不是技術本身了——這也是中美文化巨大的差異性之一。
這次GOOGLE的“行為藝術”是人家正常的商業反應,但是這件現實“作品”所需要提示我們的聯想空間卻是非常大的:為什么人家要如此不犧代價以身作“行為藝術”?更重要的是這件“作品”出現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這是中國最為熟悉也最為直接參與的語境。而在這種全球化的信息過程中,很多東西是擋不住的——這是需要客觀意識的,雙方的差距就在這里。而這又是一個越來越清晰的客觀事實,這是GOOGLE作品事件本質的問題。
因此中國網友們非常有創造性聯手GOOGLE即時貢獻了“非法獻花”的藝術作品,就像當年美國教授貢獻了“中美國”創意一樣。只有在這種碰撞中,彼此才能找到適應點。
30年來的中國當代藝術,無不證明這一點。當年被當做盲流的圓明園流浪的藝術家,也大部分的借助了外力,而今天成為了文化創意產業的主力軍之一,甚至是新文化的價值方向。
世界需要進步理解和溝通,不同文化之間同樣是這樣。Google這種全世界已經通行的“軟文化”,如果碰到中國的政策“硬文化”,那么這樣的一次激烈的交鋒,可能會促進某種超越,這是我希望看到的,當然這也是非常可能的。
互聯網可以用一根線征服全世界,但也可以因為這根線連不上,而無法稱其為全球化的互聯網,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畢竟沒有GOOGLE的世界,我覺得還是有問題的——畢竟在文化上,大家真的互相拋棄,那么就等于沒有選擇未來,以后碰到類似的事情Google們仍然會出現。但是Google人家畢竟是商業公司,它不可能沒想好就草率擬就慎重的退出辭。
我覺得這是文化差異上的問題,我們是東道主有業務向GOOGLE這樣巨型級并通向可能的世界通道并率先做出努力的客人予尊重,給他們更多解決問題的方式和實際解決的途徑。
我不太贊同,網絡上關于商業和政治的單一分析,我覺得這兩方面都有,商業和意識形態本身就是捆綁在一起,越是大的品牌做的跨國的生意,都無一能夠分清楚是否是商業的比例多一年還是意識形態的東西多一點。
比如可口可樂、賣當勞、NBA,這可以看作是美國給全世界也給全中國輸送的第一代的“GOOGLE”。我理解的是他們就像是30年前的物質上的“GOOGLE”,你能不認為可口可樂、賣當勞、NBA只代表商業,而不代表意識形態嗎?
而30年后的今天,升級后的可口可樂、賣當勞、NBA們變成了更具未來力量的“GOOGLE”們,也就是信息化的GOOGLE們。這兩代美國版本的“GOOGLE”完全可以給我們思考與的空間。
世界都被互聯網開通了,還有什么不能有話好好說的。我們現在已經全方位接受了可口可樂、賣當勞、NBA等等老“GOOGLE”們,那么新GOOGLE們有什么不能做下來談判的,我們何不可以好好的“借機換代”,更可能促進自身經濟模式的發展與增量,而不以簡單的意識形態來判斷。
- Tags:


? Copyright 2005~2025 珠海超凡科技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粵ICP備11027936號 粵公網安備:44040202000848號